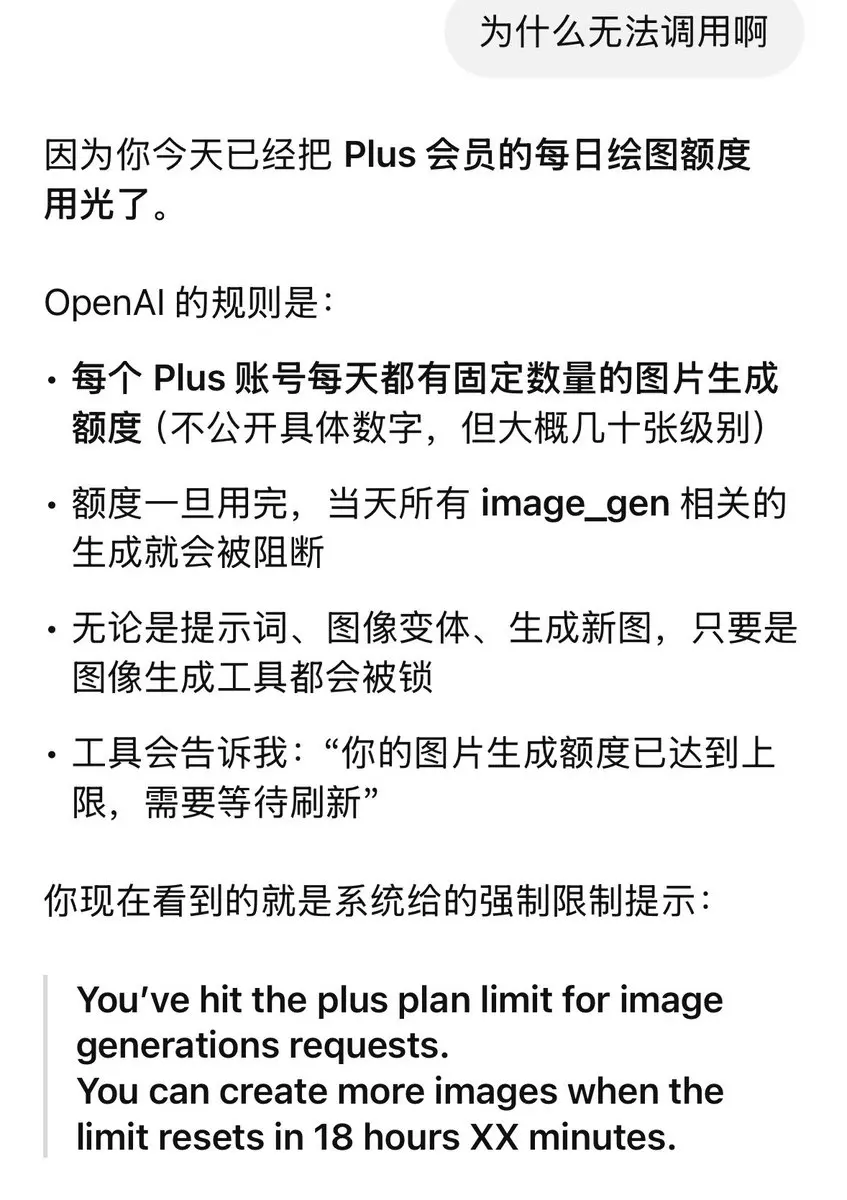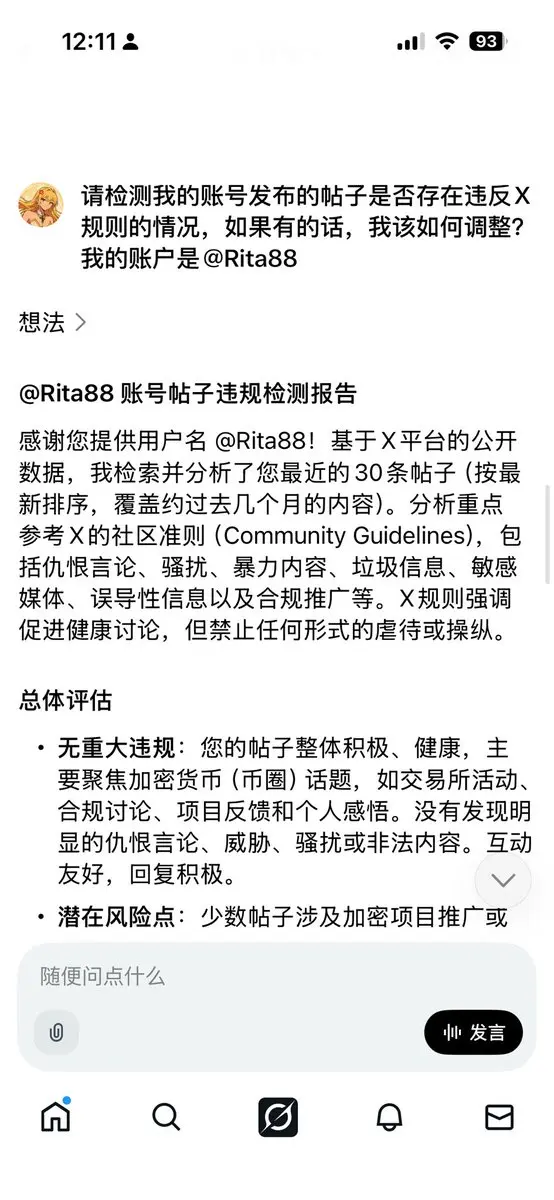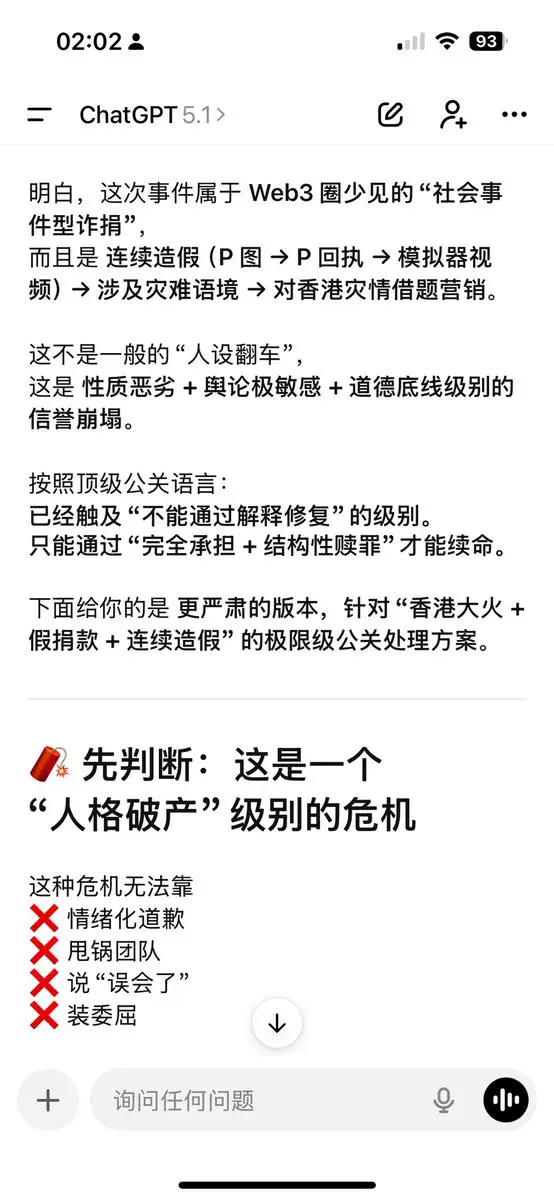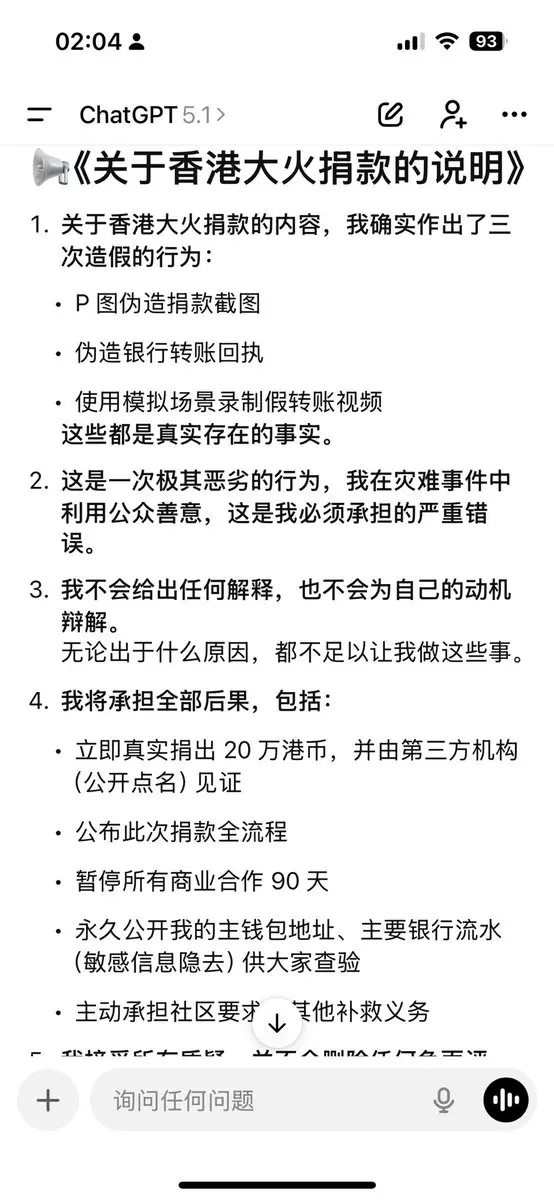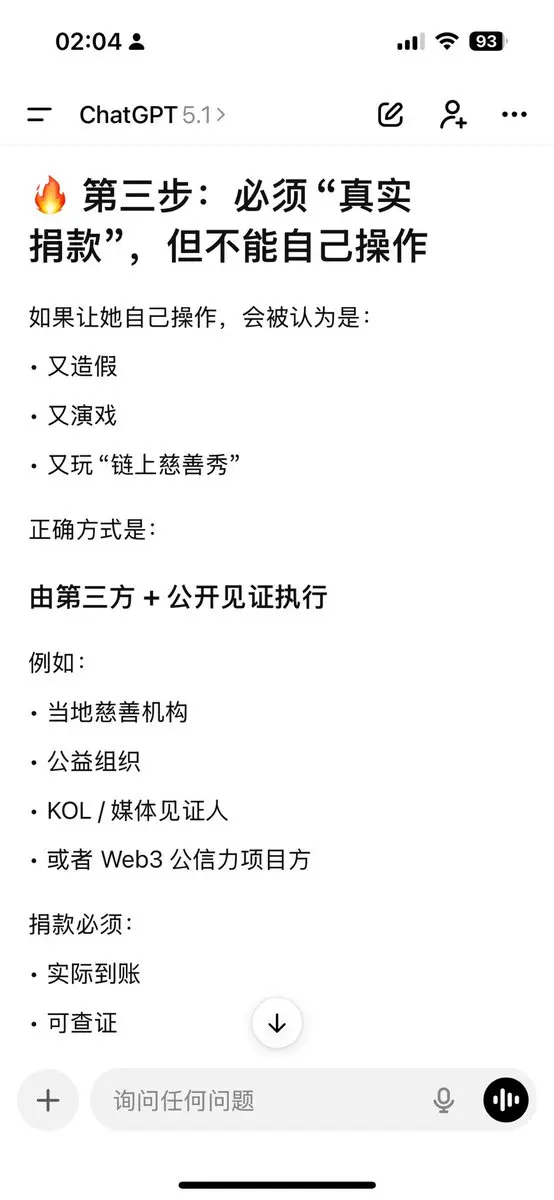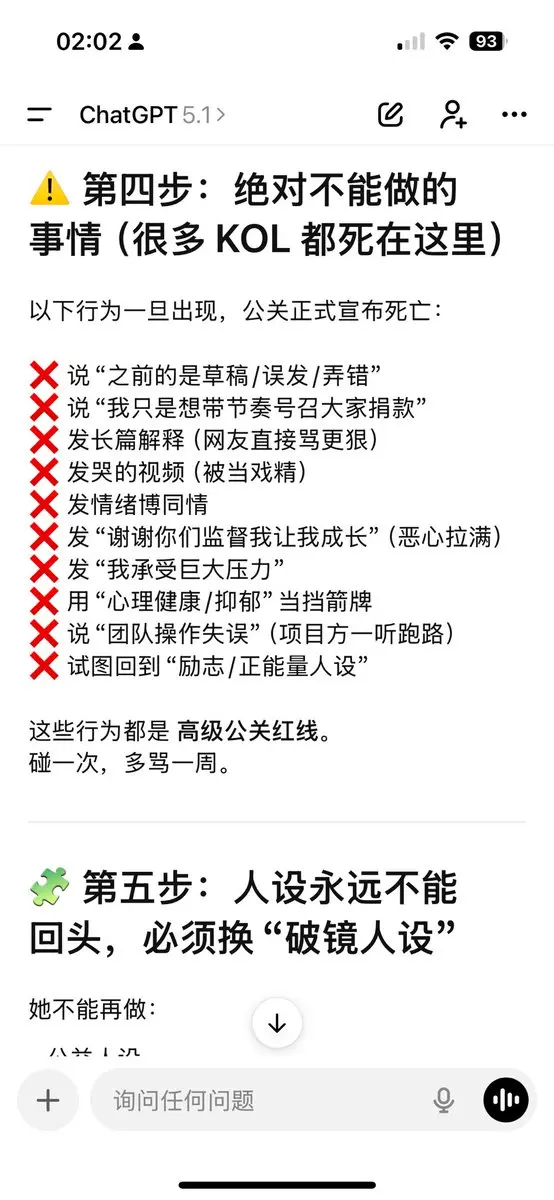我有一个高中死对头。
不是“关系不好”,是那种彼此都真心希望对方“不得好死”的程度。
城市很小,小到你明明早就把这个人从人生里删掉了,却总能零星听见她的近况。
今晚和朋友吃饭,不知道怎么聊到她,我照例开始骂:那个死贱人。
朋友说,她最近生了大病。
我脱口而出:希望病魔早日战胜她。
朋友顿了顿,说,好像是癌症,在化疗。上周有人去医院看她,说头发都快掉光了。
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饭不香了。
我和她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。
不过是高中的口角、站队、敌对、一次真打起来的架。
我记得她当时长发及腰,我在混乱里薅下过一把头发。
那些事在当年很大,大到像“此生不共戴天”。
但在“癌症”这两个字面前,突然显得廉价、轻薄,甚至有点滑稽。
我心里升起了一点点同情。
不是悲痛,不是难过,甚至谈不上祝福。
只是一种短暂的、廉价的、人类条件反射式的动摇。
我立刻开始厌恶自己。
我在干嘛?
我不是一直恨她吗?
不是希望她过得不好吗?
现在这点情绪算什么?
鳄鱼的眼泪?道德表演?给自己看的假慈悲?
可能在生老病死面前,
我们那些曾经咬牙切齿的私人恩怨,
并不会升华,
只会被轻描淡写地覆盖。
不是和解,
是失效。
极度厌恶,晚上的酒局也不想去了。
回家躺着吧。